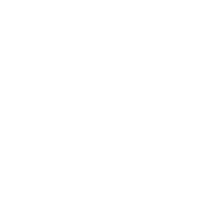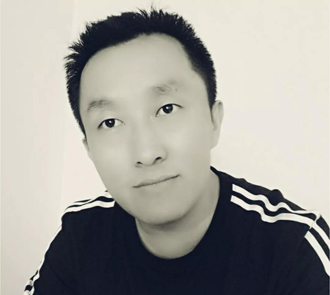【和谐中国网·和谐书院】
我的写作,不只是在告诉人关于这人间的美丽,而是在唤起一些沉睡着的美丽的心。——星月夜
作者米抗战,笔名星月夜,西安某中学教师,已发表散文若干,文字散见《读者》《思维与智慧》《小品文选刊》《新华副刊》《时代青年》等各级文学期刊,有作品入选 2015年陕西省中考语文模拟试卷,入编《读者年度选集》、《全国青年散文大赛作品集》、《陕西文学年选》等文集。
咥馍
星月夜
馍,北方的叫法,南方称“馒头”,这两个词虽指代的是同一种传统面食,但在我的情感意识中,前者远比后者更简练,更亲切,更具烟火苍苍的生活气息。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人,我更喜爱听闻前一种叫法,在上嘴唇与下嘴唇的轻触之间,一个平和温情的“馍”字仿佛能氤氲出一缕淡淡的麦香味,让人禁不住想起平阔阔八百里秦川那随风摇曳的金色麦田。
幼时在乡下,我们一群孩童时常会唱这么一首儿歌:“弄啥好?过年好!吃白馍,砸核桃……”,歌声中充满了对吃上一口白面馍的美好憧憬。在过去餐食寡淡的日子里,能咥一肚子新蒸的白面馍,也会让人浑身的关关节节都舒舒坦坦的。
关中人咥馍向来十分讲究。咥馍者不论年龄老幼,对馍的外形、色泽、口感都有着极高的审美素养。一盘馍端上来,这第一眼一定先审视馍的外形和色泽,泛黄的是碱过了,裂缝的是面旺了,起坑的是火欠了……言来语去,一时间评点得蒸馍者脸红到耳朵根儿。看似平平常常一个馍,在关中人眼里绝不止一个半球型那么简单,馍做的好不好往往会成为评判一个人心灵手巧的考卷。
从秋播选种开始,关中人就为来年能吃上一口味道纯正的白面馍劳神费心了。待新麦子磨成粉,一多半都会用来蒸馍,经发面,醒面,揉面,试碱、攒馍,蒸馍六道工序,每一道都得细心操作,万万马虎不得,方能蒸出一锅好馍。说起蒸馍,攒馍算是蒸馍过程中一道关键工序。如果说试碱决定一锅馍的成色,那么馍攒得紧不紧实就直接关乎馍的口感。一个攒得松松垮垮的馍,吃起来自然会欠缺嚼劲。在看似短暂的攒馍过程中,攒馍者须得沉下心,以指尖感知面的弹性和韧性,只有将指间的丝丝力道和对家人的殷殷爱意一点一点攒进馍里,才能将馍攒得饱满圆实,润泽发亮,才能显出一个好馍应有的精气神来。
一个馍要攒成什么样才算好看?要攒几个回合才咥起来劲道?或许只有母亲的手才知道。母亲对馍有着最朴素的审美标准,这个审美标准既关乎馍的模样,也关乎馍的口感,一锅馍蒸出来要经得起一家人口舌的咂摸,才算是口味纯正的好馍。
我自不及灶台高的时候起,就常常踮起脚尖看母亲攒馍,她沾满白面花花的手虽写不出漂亮的字,却能将攒馍的技法深谙于心,攒的一手好馍。烟熏火燎的灶房里,她弓腰凝神将一团又一团面捏进指间,在虚蜷的掌心里三翻六缠十二转,借着一股巧劲忽而一停,案板上随即就稳稳妥妥地蹲起一个姿态润圆的馍来,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不大工夫,荆篦上就围满了圆墩墩、胖乎乎的馍,好似一群招人爱怜的白瓷娃娃。待锅中泛起水花,经硬柴旺火一蒸,热气腾腾,麦香四溢,诱得人腮帮子一酸,霎时间涎水肆流,开了胃口,来不及洗手,趁热掰开一个热馍,再抹上新泼的爨香的油泼辣子,撒上细末子盐,一口气能咥五六个。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娃,没有谁不是咥着自己母亲攒的馍长大的,吃惯了母亲攒的馍,偶尔吃上一回别人家的馍,嘴就会自然而然地认生,牙与舌头也配合得不再顺溜,嚼来嚼去总觉着欠点啥?
说到底,馍在关中人的生活里,也像面条一样是三餐不离的主角,是支撑生活的台柱子。曾有人戏言道,大秦岭有多少峰,关中人就咥过多少馍。平日里,从早到晚,喝稀饭、咥扯面、咬葱嚼蒜,关中人的嘴边总少不了一口馍,没有馍的日子对关中人来说是不实在的。一年四季,婚丧嫁娶,蒸馍绝对是其中一顶一的大事,用精收细磨的上等麦粉,请四里八乡的头号把式,为得就是能蒸一锅嚼劲十足的好馍。在这些宾来客往的场面中,馍的面相直接关乎主家的脸面,待客的菜品是否合乎客人口味,往往不及一笼蒸得宣腾腾的白面馍更能撑得起面子,甚至最平常的请客吃饭,关中人通常也惯于以面打头,以馍收尾,饭后一个馍,那是对客人实打实的终极关怀,容不得接二连三的推辞。
咥啥?咥馍。最是妙哉当属关中方言中的这个“咥”字,其音借丹田之气自齿间迸发而出,讲起来语音浑厚,铿锵有力,听起来又大有斩钉截铁、气吞山河的豪迈气势。一个“咥”字出口常常能瞬间激起人的食欲,继而无论黑馍白馍都能咥出高兴,咥出欢乐,咥出幸福。“咥”字之于馍正如“吼”字之于秦腔,其所彰显的正是关中地区千年积淀的秦风秦韵,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字,那感觉就会绵软无力,那浑厚的底蕴就会大打折扣。
咥的意蕴三言两语道不尽,但咥馍的气势却人人都能展现:一个馍捏进手中,寻合适地儿一蹲,提眉瞪眼,大嘴咬满满一口,继而圆鼓着嘴细嚼慢咽,任由丝丝麦香在舌尖与齿间漫漶……以这般豪迈的吃相去咥馍,三下五除二,好几个馍就下了肚,大有风卷残云之势。在关中这片土地上,一个能咥又能干的人常常被人们视为生活中的英雄。平日里,顶风冒雨出一趟远门,或迎着太阳下一回地,只要是地道的关中人都会随身带着几个馍的,这一习以为常的举动并非懒得做饭,而是为了挤时间赶活计,跟平平淡淡的日子拼劲头。每当行远了,干累了,啃几个馍,灌几口水,迅疾就能重新恢复体力,继而一口气忙活到日薄西山。
有馍在身,日子不愁,惯于随身带几个馍奔日子的关中人,个个都是能受得起天磨的铁汉子。自苦水窝窝里里一脚一脚趟出来的关中人,从不认为干咥一个馍的日子有多么不堪,倒是大鱼大肉之类的吃食反而会让人的肠胃起腻。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在离家十多里路的建陵镇上中学,学校离家远,吃不上热乎饭,就只能背上满满一包蒸馍,再带一罐头瓶咸菜去上学。那时候,学校里没有食堂,只有一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锅,每到饭时就烧一锅开水,供同学们自助一碗“开水泡馍”。一只洋瓷碗,一个蒸馍掰成块,再倒上开水,汤汤水水,热热乎乎,是我那时常吃的一餐,从初一到高三,一吃就是整整六年。
夏天,新馍过不了周三就泛起浅绿色的霉点,有时还会生出长长的绿毛,扔又舍不得扔,泡在碗里会冒出浓浓的霉味,实在难以下咽,全凭着一口口咸菜下饭。照这样的吃法,往往一周刚过半,一瓶咸菜就吃完了,余下的馍就只能清汤白水地往下吞。后来,总结出了“三一”定律,即强忍着吃三口馍之后再就一口菜,这样吃来竟别有滋味,因为上一口菜与下一口菜相隔得远了,每一口都充满了期盼,忽而就觉着咸菜是那么的香!冬天,馍又冻得干硬,掂在手里像个铁疙瘩,要将它掰成块就更难了,干硬的馍皮常常会划伤手,留下一道殷红的血口子,寒风一吹生疼无比。冰天雪地中,不等一碗“开水泡馍”吃完,水已经半温不凉了,吃进嘴里的馍块,一口比一口寡淡,一口比一口冰凉。有时候,烧水的师傅生病不上工,我和同学们就只有接半碗凉水,硬生生地把干硬的馍一口一口逼进喉咙。
在那段艰难困顿的岁月里,每日吃着这样粗淡的餐食,让我常常觉着自己就是路遥笔下的孙少平,除了个头没他那么高,枯瘦的身形、深陷的眼窝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直至高中毕业,我的体重还不及一百斤,乡亲们见了都戏称我为“干柴棍”。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,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,可是学习的劲头却从未减弱,反而更加拼命,每天熬夜读书写作业到凌晨也不觉着疲累,甚至周末回家陪父母干农活,也从不短精神!
老辈人常说“苦日子锻造硬脊梁”,回想我所经历的那一段“开水泡馍”的困苦日子,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。
“秋播百亩田,夏收堆满仓,蜕皮留麦粉,蒸馍万里香。”
回顾平生,咥馍无数,那圆乎乎的馍在我心里早已发酵成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乡恋情结。
在当下衣食无忧的好日子里,尽管餐餐有肉都已不算是什么奢望,可我还是会时时念想着那麦香醇厚的白蒸馍,尤其忘不了母亲亲手攒的口味纯正的手工馍,和那新馍刚出锅时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。
【和谐中国网】投稿、广告:
邮箱:731590068@QQ.com
微信:131 4145 7599